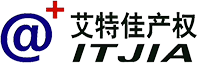《四千年农夫》介绍
最近受朋友的邀请参加一个读书会,介绍《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此书是我和爱人五年前翻译的,为了在读书会上介绍这本书的情况,笔者重温了这本书。
《四千年农夫》一书之所以在有机农业领域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应该源于它是最早出版的一本反思西方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的农业耕种形态并介绍东亚持续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书,金在书中交代了他来访东亚三国的目标“我们渴望了解经过两千年或三千年甚或也许四千年之久的今天,怎么使得土壤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三个国家稠密的人口成为可能。”
百年之前,美国因殖民化形成的大农场农业耕种模式,就已经面临种种困境: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不可再生能源投入;百年之后,美国农场数量急剧下降,农场规模愈大也就愈依赖农药化肥农机投入,农场陷入“要么变大,要么走人”的困境,乡村地区的社区愈加衰败。
书的作者是美国土壤局局长,他于1909年2月2日离开美国西雅图,7月下旬返回,在中国停留约为4个月20天,在太湖流域前后两个半月,还访问了香港、珠三角和西江流域、青岛、济南、天津、长春,金考察了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在他的书中反复提及的核心观点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城乡之间、乡村内部进行的物质循环,特别是农业与人的衣食住行的关系,文中的描述让传统农耕社会的图景展现在眼前,“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中国传统农业倡导的“种养结合、精耕细作、地力常新”,核心就是处理好农业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农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农人则需要处理好这几个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便是农事的管理。
这让我想到很多人经常会随口说:“我都种了几十年地了,不用农药化肥会颗粒无收!”这样的描述其实也反映了农人了解物候、增强地力与作物管理之间的关系,农业耕作技术正体现在农人对这三者关系的把握上,技术当然也就有深浅之分,并不只是跟从事农业时间长短有关。正像我们通州顺义两个蔬菜种植基地的技术员郎师傅和马师傅在同样种植一种蔬菜上,尽管都是有机的耕作方式,但还是存在着技术的差异,进而会影响产量。这种差异本身来自于经验。这也说明仅就耕作技术本身而言有机耕作技术并不能与常规耕作技术比较优劣,无论有机耕种还是常规耕种,农业具体操作中的差异性都是巨大的。
在中国传统农耕思想中,施用肥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肥土壤”,而不仅仅是美国农业模式中满足微观上营养的需求,中国农耕的思想是整体性的。本书中就提到了当时使用的十几种肥料:人粪尿、家畜禽粪尿、蚕屎、蚯蚓粪、草木灰、草木落叶、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秸秆、蜗牛壳、豆饼、灶灰等,同时书中还描述了中国农民种植技术的核心准则是“如何集约有效利用时间和空间”,因此像间种、套种、一年多熟、轮作等,都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产出。
当然,作者在中国的四个月也体验了不少中国的风土人情,农业提供给了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原材料,养蚕、种茶、种烟草、建筑、燃料、织物等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乡土生活有关的就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乡土文化,诚实、节俭、幸福、满足、忙碌、平和……这次词汇所描述的那个时期中国人生活虽然不能从书中黑白照片中看出来,也肯定有人会说金浪漫化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在农耕文明的条件下,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与土地近了,人类无论是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条件下,都会更接近自然的节奏。生命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和心理反应,而时间是所有这些反应的函数。农民就是一个勤劳的生物学家,他们总是努力根据农时安排自己的时间。
(百年后的今天,农民被远远的抛在了激进现代化浪潮的后面,社会反应条件已经大不相同,能够认识农民的价值以及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都与百年前大不相同。此处,书的作者及笔者都没有下价值判断。)
费孝通读过此书后写道:“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
有机农业的阶段式发展
很有意思的是,在金完成了这本书之后,一个英国的土壤学博士霍华德被皇家派往印度教授农业耕作技术,在印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却产生了对英国农业耕作方式和科研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并完成了同样对有机农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本著作《农业圣典》。
之后,鲁道夫史坦纳、罗代尔、福冈正信代表的生物动力农业、有机农业、自然农法等都有相似的核心思想,只是在技术操作上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这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到有机农业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是寻找最纯净没有污染的食物,就像很多人都会问:“北京的空气都污染了,怎么种有机?”其实这个问题里混淆了有机农业和有机认证的产品之间的差别.
这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7080年代,都是各类有机农业思想、哲学发端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面临问题的背景是西方大农场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能够让农业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这是这个时代农业思想孕育的基础。这个时代也被称作有机农业的1.0时代。
有机农业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百年来在西方仍在加剧,20世纪的60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发展代价的转移,农业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也就随之产生了对有机农业更大的产品市场需求,这个时期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立了不少民间有机农业协会,也有不同的区域联盟的生产标准,也就产生了标准不统一造成的贸易困难,因此,在7080年代,各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开始出现,不过,这些国家标准基本都是参照了行业内的不同区域的标准,也是对有机农业各个不同利益主体的平衡。有了标准,也就容易形成市场规模,1970年代到2010年代,这段时间是有机农业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在有机农业运动舞台上都更多活跃着有机产品的进出口、国内市场开拓、大型展会等现象。这个时代有机农业的特点是有机农产品更为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这个时代也被称作有机农业的2.0时代。
当然这个阶段也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有机农业也被工业化,为了压低生产成本,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美国很多大型有机农场都会雇佣墨西哥非法移民工作,很多人认为有机农业在这个阶段偏离了“生态、健康、公平、关爱”的四大原则,尽管有机产品对消费者有了更多好处,可是公平关爱的理念并未在有机农业体系中体现出来。也就是在有机农业体系里经济又脱嵌于社会了。还有一些关于有机农业标准降低的讨论,很多人认为有机农业的标准降低是为了不断扩大国内有机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比如是否允许使用转基因的种子的问题。还有很多人认为有机认证本身简化了有机农业的思想,在认证标准中仅能体现对种植方式的要求,而没有体现有机农业对人与人关系特别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思考,一件商品是否体现了四大原则中关爱的原则,或者说关爱的原则是否可以被标准化,这也是这个阶段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平行于有机认证的第三方体系TPS的另外一种有机农业认可方式参与式保障体系PGS,这个体系最早出现于巴西的一次有机农业的会议上,很多人提出现在的有机认证重新割裂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而变成一个中间获利部门,应该有一种新的认证体系被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拥有,而认证过程对于双方来说的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巴西、印度、新西兰、美国有了国家认可的PGS体系,他们所认证的产品有的可以贴“PGS有机”的标签,有的只能使用“生态”的标签。在有机农业2.0阶段的1970年代在欧洲和日本还出现了一种倡导“直销、当地、友好”的产销模式,在日本被称为“teikei提携”,在美国被称为社区支持型农业CSA,这种模式本身因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长期的关系,很多人认为CSA模式本身就不需要包括PGS模式在内的认证。在中国,我们将这类模式统称为“社会化农业”,意即区分于产业化农业只重视经济功能的模式,产业化农业只是将农业看做一种生产方式,农产品看做一种商品,而忽视了农业的环保、生活、休闲、就业等其它方面的功能和价值,社会化农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农业生产和流通方式,2008年后兴起的市民CSA农场、农夫市集、消费者共同购买等模式都属于社会化农业的类型。
2010年起,在世界有机农业的舞台上更多的农场主越来越活跃,他们提出有机农业应该回到关注生产者的本质上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主席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有机农场农场主。于是,有机农业3.0时代出现,这个时代仍然会发展有机农产品贸易的部分,但会更多回归有机农业四大原则的核心部分。这个3.0时代,我们看到IFOAM开始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CSA,降低认证成本让更多小农加入有机农业运动的PGS参与式保障体系。IFOAM曾经与CSA国际联盟URGENCI谈判希望将URGENCI变为IFOAM平台下的一个分支机构,但这个提议被URGENCI理事会否决。IFOAM后期对于PGS的推动力度越来越大,在2014年土耳其的第18届国际有机农业大会上,专门设置了会前会讨论PGS的发展,并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将国际PGS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派到中国来交流一段时间。
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呈现有着与西方不一样的内容。如果将现代话语中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作为首要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乡土文化则是在这个标准下最高的文明形态。农业在乡土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文明的形态下,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少数对多数的“剥削”,如若农业价值高,城市不能再源源不断向乡村抽血,则城市化本身的低价劳动力就难以获取,中国农民安土重迁,如果能在乡土获得一份足够体面的收入,并不一定想要进城务工。而乡土文化本身的正外部性并不能通过经济效果去简单评价。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政策导向仍然沿着不断城市化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多的乡土社区被破坏,则城市也要为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成本。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农民不能再依赖土地为生,只能进城务工,成为城市里的打工者,多数在建筑业;低价也给予城市人一个维持城市生活的低廉生活成本,都市的生活消耗着无数“低价”的产品,从食物到服装,而这些低价的产品却有着极高的环境和乡土社会的成本。因此,有机农业在中国不应是简单的对农业生产标准的一种认定,更应该包含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和认可。中国有句俗话:“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人的欲望无止境,只靠人类自己的道德约束恐怕要求太高,而保护和珍视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抱残守旧,这反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大道中庸”内涵的发展。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瓶颈
有机农业的发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将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贸易产品,那么有机农业的发展也一定会走上如现在“产业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困境,那就是发展不知为了什么,这些化本身都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如果为了化而化就一定会出现,为了使用大型机械而流转土地,让小农无法生存,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农场手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量的农业支农资金补贴的方向基本上都给了大型农场,而拿到这些补贴的农场因为与农产品收益相比非常简单就能拿到,也就越来越不重视农业的生产,进而我们看到大量受到补贴的项目越来越多荒废的设施,与此相比,真正承担质量和产量基础的小农户却很少能拿到补贴以及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
如果说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根本其实是保护乡土文化,则必须要给予这些小农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支持,以及技术公平有效传播的方式。农民作为一个生产主体,选择种子、农药、化肥等投入品,所获取知识是在地化的还是受到被专家学者大农业公司垄断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有机农业的困境是由于农业政策本身都是有利于工业化农业发展的模式的导致的,而推动多样化、非标准化、小规模、本地化的农业政策非常有限,方向不是让大公司进入替代看似“落后”的小农户,而是给予农户组织的基础,形成合作对接市场,真正把农业的方向放在让农民通过农业可以生活在乡村并且维持一个乡土社会的稳定基础上,让政策如何切实有效落地,降低农业部门利益在其中的影响。政府直接对接农户的确交易成本会很高,那此时就必须允许农户的行业组织或者协会的建立,政府转变服务观念变为行业组织的服务者和利益协调者,这样也不会再形成政府总是变为危机的应对主体,每次一出现“草莓农残过量”的事件,政府就需要应对,反而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解释。
有机农业倡导:公平、健康、生态、关爱这四大原则,希望在有机农业3.0时代回到有机农业起源地中国,重新探讨城乡关系、生活方式、生态价值。